- 资质:
- 评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8分 9分 10分 10分
- 印象:
- 经营时间:11年
- 展厅面积:300平米
- 地 区:上海-杨浦
自在之外·艺术的根源性构造
“自在之外”是一种程式,必须通过这种程式,艺术才成为可能——颜料、石头、声音、镜头乃至日常生活用品,这些形式各异的存在物在创作者手中能磨合成为杰出的艺术品,都是因为艺术家在使用它们进行创作之前,产生了一种自在之外的兴趣,即超出存在物自身的规定看到了逾越于它们本身之上的东西。
如果我们给定绘画一个要求:绘画必须尽最大可能将一个对象复制得如其所是。那么这难免让人产生困惑,因为作为一个对象,它是一个人,同时又是一堆碳水化合物,原子的排列体,一些简单的图形,同时又是一个农民,一个佛教徒,一个勇敢者,同时又是你的朋友……它是所有的这些,那么它们其中究竟哪一个可以作为那个被规定的如其所是的对象呢,或者说究竟应该以哪种作为描绘对象的存在方式呢,我们不可能将所有这些存在方式都同时再现,因为愈是这样,就愈会与前面的要求背离。
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划分:以原始的质料和形式为依据,碳水化合物、原子的排列、细胞聚合体被划分为一类,而以概念和理念为依据,人、农民、佛教徒、勇敢者、朋友被划分为另一类。那么,具象的作画方式就有两种——第一种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有形的物体,我们忘记它叫什么,无论它是桌子、板凳或者是花草树木,在我们眼里统统都是一堆结构体,是点线面、空间体积的聚合物,对象在社会中的现实意义以及它在我们个人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完全不在考虑之中,虽然画出来的东西是具象的,但这是一种抽象的思维;第二种是,我们牢记它们的名称——桌子、椅子、苹果、花瓶,而且坚持自己画得是一个苹果或椅子,而不是一个圆和一个矩形,或者我们还将人的概念解释为战士、农民工、社会青年、上班族,并且对这些物象产生自己的分别看法,而把这些看法表现为画面的文本,符号化的象征手段总是孜孜不倦地被用于这种表现,尽管我们手中所干的事情永远是组织一些点、线或者色块,但是我们心里想的却不是点、线或色块,而是它们加在一起所是的东西,是那些作为理念的物象,是一些由知性在很远的经验中形成的概念。
我们的感觉器官通过直观从外界(显像中)获得表象,通过知性整理而得到概念,我们实则生活在一个概念的世界,我们被一些名称所包围,一旦丧失了这些名称,现实中的一切事物将于我们毫无意义可言,因此,作为概念的世界和本体世界是分离的,比如——斧头、皮衣、儿童玩具就是存在于概念世界中的物,这些器具是因为人的某种生活目的而被打造出来——人凭借纯粹理性将各种质料按照一种有用性的目的而做形式化整理,人们把一堆无用的废铁做成可以噼材的利斧,把动物的毛皮和棉布制成衣服,将一些塑料和金属片制成儿童玩具等,这些东西在它们被制成之后与它们被制成之前相比,其质料的原初属性丝毫没有改变,而只是形式被改变了,而且正是因为这形式的改变才使它们具有了有用性,但是有用性必须依赖于它的可靠性(主要是器具的耐久度),器具的可靠性是在其使用过程中不断流失的,因此任何器具都要有一个使用寿命,只有在这个寿命期限内,器具才能是器具,而任何超出这个期限的范畴——无论是在它被制造以前还是在它被遗弃之后,都不能算作器具本身,而只能是那堆原材料。在这里,器具是与人相关联的概念王国的那部分,原材料就是作为本体世界的那部分。
作为概念的具象事物并不在真实的环境中存在,概念本来是如幻性空的,它只存在于与人自身的联系中,它的存在对“我”而言至关重要,可以对“我”产生生活上或精神上的影响,可以便利“我”的衣食住行,或者丰富精神生活,于是它便存在了,而且人的主观情感与这些作为概念的事物紧密相连——一个孩童会因为自己心爱的玩具被摔坏而感到伤心,一个成年人则会因为自己的收藏品生锈而感到惋惜,人们很容易对一个短暂的聚合的生成产生常见,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恒常的可以被称作是它们名字的物存在。生命本身也让人如此,一堆原子按照某种规律排列,就聚合形成一个生命体,但是在下一刻,它们各自分散然后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整体,马上聚合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体,而这个生命还是上一个生命吗?所以,作为概念存在的物是那些永远变幻着、消逝着而却绝不真正存在的东西。
和人造器具的思维一样,我们按照具象绘画的思维,用最简单的点、线、面来描绘我们心中的概念世界,自在之外被作用于这些点、线、面,我们看到了超出点、线、面本身的东西——这些最原始的质料被转换成为它们加在一起所是的东西,于是生成具象(作为聚合的概念)。但是,对于艺术的要求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倘若一种自在之外的结果是某种功利目的东西,那么这就不得不跟人造器具的过程一样,最后被造作出来的是工具,是有着某种实际用途的东西,而并非艺术作品。假如我们仅仅是为了在画布上再现一个桌子,而并不为了其它,那么我们所做的只是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竭尽所能复制我们所看到的桌子,使画面上的桌子看起来跟实际的桌子更为接近,而且尽管我们事先知道我们的复制无论怎样接近它,也始终无法等同于它,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乐意去相信自己制造的这幻觉,并感到成功的喜悦。这是一种有为的喜悦,它符合我们的目的,即要使画面上的桌子更为接近实际的桌子,从而使观者读不出它们反射在人眼的光线中的差别,这是一种有功利的游戏,而且限制了艺术的自由,它使得我们的动作无不被客观对象制约着。
于是,一些画家们便开始思索改革,他们开始思考如何让画布上的自然与真实的自然变得有些不一样。在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尽管所有的人们都竭尽所能仅仅去复制对象,但每个人所复制出来的东西却还是会呈现各式各样的区别,他们根本用不着去思考如何让他们所复制的跟真实自然变得不一样,它们就自己区分了开来,这个现象向所有画画的人明示,绝对复制自然是完全不可能的,每个人所看到的都只是与每个人各自的感官结构相关系的显像,正如叔本华说得那样:“他不认识什么太阳,什么地球,而永远只是眼睛,是眼睛看见太阳;永远只是手,是手触摸着地球。”绝对的自然——作为自在之物,是无法捉摸的,创作者无论如何去摹仿他所看到的自然,都不可能从中描绘出事物本来的样子,而永远都只能是处于自在之外的状态,主体的思维在有形之物之上达到了另外的提炼。
既然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这种处于自在之物以外的,与之相分离的描摹状态,那么这样一种对绘画的规定“绘画必须尽最大可能将一个对象复制得如其所是”就变得意义甚微,很多画家都明白这一点,他们认为在画布上显现一个物体A,那么它就应该是现实中的物体B加上其它的什么东西C,即A=B+C的原理,而并非A=B,C是作为B的自在之外的产物,它作为一种额外的特殊目的(并非功利的),以B为原初材料发生的一种内在生命的投射,或者可以仅仅理解为一种具有探索性的兴趣,那么艺术创作这种行为就是按照这种兴趣的要求,以日神的方式来进行的游戏。
这样看来,拟定游戏的性质是否是艺术,关键取决于C的属性,或者说取决于发生于B的这种叫做“自在之外”的程式的发生类型,而与B本身到底是什么没有关系,它完全没有必要一定是一个具体的对象,或者某个具象的概念,甚至一种毫无意义的东西便已足够。音乐最能说明这一点,作为一个音乐作品A,它的原初组成材料仅仅是一些单个来说简单的音调,而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一种音乐:所有音调相加起来的声音等同于自然界中的动物所发出的声音。音乐家们从来不试图去摹仿自然,他们对各种单音进行形式化的整理组合,和具象画家们对点线面进行形式化的整理组合不一样,虽然无论是音乐家还是具象画家,他们大脑中所思考的都不是那些原初的质料——音调和点线面,但是音乐家更多的在于,他们所思考的并非是所有音调加起来所是的那个东西,而是与所有这些旋律完全无关的事物。而且,尽管他们不凭借自己的乐声去摹仿自然界中具象的声音,但是那些想象中的事物却可以是具象的,比如一位作曲家在完成一部壮阔的交响乐时心中所想可以是一个悲剧英雄的史诗故事,这种想象中的具象就与具象绘画中“加在一起所是的具象”非常不同,因为它在所有这些音调的综合中找不出任何与之相关的线索,而具象绘画中“加在一起所是的具象”所依赖的是我们从很早的经验中获得的概念,凭借着这概念,我们才能超出画面中的点、线、面去看到具体的事物,因此,音乐的这种自在之外更加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
多数群众喜欢观看写实绘画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视觉早已习惯于看到现实生活中各类的具象事物,而这样一种将形式的杂多整理成具象概念的习惯则是在很早通过经验被保留下来的,因而他们只需要一看到画面,就会不自觉地根据这种经验的习惯去进行审美判断,从而把寻求感官的相似度变为绘画的唯一乐趣。
一种纯然的艺术感受必须是从心灵出发,虽然达到这种最终的体验结果需要很多经验元素铺搭桥梁,但是这些元素绝不会是C中所包含的,所以,我们尽管不能把这种对相似度的追求作为最终的艺术目的,但可以在保留它的情况下进行某种额外的形而上目的。具象写意绘画便由此而来,那些心中包含有具象概念的元素,但其最终目的却不是表现概念的创作者便属此类——后印象主义、表现主义都属于这种具象写意,但不包括康定斯基,就算是其早期创作的色彩斑斓的具象画,也不能算作此类,因为它属于我们在前文中的第一种分类:它忘记了对象的名字,而只记得点、线、面,也就是只记得原初的质料,而忘掉了概念。因此,像这样的,即便是最终表达为具象的绘画,却不被算作是具象写意的,而只能算作抽象的具象绘画,立体主义诸如毕加索也属此列。而莫迪利亚尼,这与毕加索同时代的画家却属于第二种,不忘记概念的,他把他的妻子作为唯一的绘画对象,是典型的具象写意派的创作者。
具象写意作品还包括一些雕塑和装置,而且它们同时也可以是观念艺术。东西方的古典雕塑作品自然不用多说,在某些装置作品中,艺术家虽然抛弃了从质料的相加中获得的经验影响,但是却在其它方面找到了替代品,比如在隋建国的作品中,红色被用来代指中国,霸王龙被用来代指西方的征服式的文明(他们自古以来就有着对自然的强烈征服欲),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红色不是一个相加的概念,它的存在方式是最原初的质料,而看到红色想到一个古老的国家则凭借经验下的意识形态才能产生,因此在这里,这种由经验获得的观念取代了产生概念的相加原则,在这样的作品中存在着把观念作为原材料的自在之外,而且它们大多数都很复杂,既掺杂着各式各样的观念,又有具象概念的成分在里面,就《中国制造》来说,“霸王龙”作为一个概念,这概念里所规定的内容与其它联想结合形成一种观念,而与红色被意识形态所给予的观念相作用,在它们这两种文本的相加上产生了一种自在之外。
全部传统音乐和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至少是被传统化的这些)都属于纯写意类作品,而不是具象写意,因为它们都是追求直接在最原初质料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它们的相加上产生自在之外的兴趣。因而它们完全脱离了经验因素的影响,它们丝毫容不得任何经验元素来铺搭桥梁,哪怕是赋予一个单色块意义,也必须是出于最自由的原则——这种赋予必须在之前没有得到过任何暗示,它既不是任何人教给我们的,也不是我们自己在某一刻通过学习获得,而是在当前通过某种想象或自我意识产生的。从对观众的影响而言,这些作品不是为了让观众去读某个文本(概念或观念),而是让观众去感受,例如我们在听到某部交响乐时感受到宇宙的浩瀚和人类的渺小,但事实上从那些音调旋律的形式组成上我们根本无法找到任何与“宇宙”和“人类”相关联的东西,它们并没有给予一个具体可读的文本给我们。
具象写意与纯写意的这种区别在告示我们,概念以及在意识形态下所产生的观念并不是艺术的必要条件,就像火柴和纸张并不是火焰产生的必要条件一样,它们只是借以燃烧的材料罢了,只要是可燃物都可以达到这种材料的要求,而艺术的材料必须可以是任何对象,而达成燃烧的那个必要条件,那个类似于氧气的东西则是来源于我们心灵的形而上补充。
下一篇:柳力:论任性

 庞明璇
庞明璇 未知
未知 张大千
张大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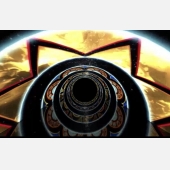 钟飚
钟飚 测试艺术家
测试艺术家 卢延光
卢延光 雪山静岩博
雪山静岩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