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友善—转换的尴尬
2014-04-16 16:12:59
转换的尴尬
于友善
【摘要】 历来纠缠袭扰于心头笔端的物象和笔墨孰轻孰重谁主谁附的问题一直困惑着画家,对于他们、对于他们的作品来说,几乎很难取舍:既不愿忽略客观物体的自然属性,也不舍得抛却笔墨表现的主体意识;如何融合好两者之相互关系,使之在一幅作品中互为映衬、相得益彰,构成既刻画了生动鲜活的自然物象又表现出淋漓酣畅水晕墨章,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如何将客观物象转换成笔墨表现的主体意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转换”过程是否称心如意,能否达到画家预期的效果,个中滋味恐怕是难以琢磨且令人尴尬的。但也许正因如此,同时它也是令人着迷的。
关键词: 物象 笔墨 符号 悖逆 相融
但凡有些笔墨体验的人都知道,对着实景画水墨往往会陷入两种尴尬:要么太过拘泥于物象而生硬刻板,要么漫笔挥洒而和物象毫不相干。前者常常由于眼前的景物(不管是人物还是景色)特具绘画感——一如人们通常所说“人如其画”或“景色如画”——眼前的物象本身散发出一种天生的摄人心魄的魅力;其形状、颜色、动态乃至神情恰巧符合画者家心目中期许的对象,似乎无须再作任何的添加或删减。而置身于这样的物象前,画家生怕忽略了那些精彩鲜活的动人之处,在捕捉这番景物时自然会生出一种唯恐遗漏或偏差的紧迫感。在这样的心理催迫下,运笔落墨不由自主地和物象的外在形貌渐行渐近,以至于走笔过程中顿生些许的滞碍和别扭。结果收笔完稿后,画中的人或景在外形表象上贴近了对象,形色体貌与表现对象相差无几,可正由于这种“贴近”,重重地损害了最初诱发画家展素挥毫的动人之美,生气全无。而后一种情形则是:面对同样的物象,搦毫涂抹之际置眼前生动而富灵性的景色与人物全然不顾,在一种欲图酣畅淋漓、潇洒恣纵的激情驱策下,任由笔下的干湿浓淡、曲直方圆一路抛洒开去,结果画面满纸废墨。且不说本该为之立照存像的物象模糊虚无,更谈不上笔精墨妙,依张彦远之说“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之像形更是荡然无存。这前后相悖的两种尴尬想必许多画家都曾体验过。这是中国画尤其是写意画一个恼人的坑坎,同时也是写意画引人入胜之精妙所在。要调和(或称控制)好两者的抵牾,需要画家在观念意识和表现手段上具备一种超越的转换能力;而能够掌控和驾驭这种现实物象纯客体的自然属性与绘画技能熟练地驰笔运墨的主体意识之间相谐相融的转换,须是高手——眼光高、手段高,那种见物生画的欲念和能力熟稔于胸、驾轻就熟而无需在运笔过程中再去生出别的杂念。
然而,如同任何兼具技能与学术属性的事物一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一个画家临案搦管展纸挥毫之际,脑子里免不了要同时思考物象之形貌神气、笔墨之枯湿曲直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搅合在一起同时同域地出现,肯定会相互抵触、相互悖逆;很多情况下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他。这时候与其说是“胸有成竹”依我看倒不如更像是“心揣乱麻”——就画而言,哪个都重要,笔墨与物象都想唱主角儿;就画家而言,一个也不愿舍弃:表现的对象毫无疑问是早早就选定落实了的,是画之主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余一切都是围绕着它来服务(应该说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事情果真的这么简单就好了,此时如果真的将笔墨闲置不顾、甚至漠然处置,带来的后果肯定是什么都不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不知大家在意了没有:齐白石的虾人人都喜欢,老百姓往往赞叹画中之虾的活灵活现——“像真的一样”;专业人士则激赏表现虾的那几笔墨色线条美轮美奂。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同一内容的欣赏,由于观者角度的差异,最终的结果如此悬殊?这里千万别用什么“雅俗共赏”来解释——这句话通常是用来骗别人、哄自己的。其实,假如我们回到问题的原点,仔细耐心地端详揣摩齐白石笔下的那些虾,打量琢磨甚或拆检每个部位的构造以及构造那些部位的浓笔淡墨之相融相谐的天作之合(当然,此时的前提必须是观者有一定的笔墨体验)恐怕就不难辨析出个中端倪了。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了解问题是一回事,解决和把握问题的内在关系并圆满处理则是另一回事。观察与分析固然重要,但远不是目的。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样一类人:辨析诠释绘画现象与笔墨原理丝丝入扣,很地道、也很在理;远非那类空泛枯燥之夸夸其谈者堪比。但反观其操笔运墨则全然两码事:要么物象不是僵硬就是虚无;要么笔墨不是呆板就是墨猪。之所以如此,我至今也没想通——但它给了我一点启示倒是更印证了先前的想法:做的远比想的和说的都要难得多。这里不想去讨论那些早已被翻来倒去说道的有些烦人的所谓“形神”关系,也不想赘述诸如“骨法用笔”之类的问题;更无意于探究那些玄之又玄的哲学、美学等深奥晦涩形而上的问题。多少年来,人们津津乐道于这些既理不清却越绕越乱的不着边际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问题,以至于到头来本末倒置地将这些本该是手段的东西拿来当做终极目标来摩挲盘玩。我所感兴趣的是,既然如前所述“白石之虾”引发的现象摆在面前,我们平日里的水墨体验也必定接触到这些问题,倒不如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琢磨它、研究它。想多了,看多了,画多了自然而然理清楚这实际上是一个“转换”的问题——由物象转换为笔墨、客观物体之自然属性转换为主观意念之自我意识。也就是说,眼之所见心之所念的纯客体物象如何通过画者之笔有模有样且生动出神,更重要的是描绘那些物象的线条、墨块、颜色及其相互构成之笔墨形象分外地赏心悦目(以至于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个‘笔墨形象’比之它的原型——客体物象更让画者着迷,也更令画者头疼)而这个“转换”多少年来折腾了多少画家、评论家。尤其是画家,终日里为其迷惑、为其困扰——要么被什么“以神写形”、“以形写神”弄得一头雾水;要么稀里糊涂上了“逸笔草草”的当,再不就死扣硬磨地盯着笔下的物象谨小而慎微,更有甚者,听闻某大师说过大可以“法无定法”便肆无忌惮地置“物象”、“笔墨”两者皆可抛,胡捈乱抹一气;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实,人们心里都明白,这些不是个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泄气的表现,纯属无奈之举:很多时候因着绕不过“转换”这个坎儿,为了摆脱尴尬,回避困扰,只好避重就轻——攀不过这座山,我就绕着走。久而久之便视手头那番活计为看家本领,信以为真自己已经觅得真经法宝,走南闯北,登堂入室;更有古道热肠的还好为人师,授道解惑、替人指点迷津,等等等等。充其量为我们祖国湟湟的美术长河无端地飘洒了些许的废纸片儿,徒然增加了后世美术评论师们筛选剔除的工作量。(这不免有点自私)
话道这里,似乎是绕进了死胡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原地站着不动更不是。但若细细想想,“转换”意味着拐弯儿,并非碰壁;问题是这个弯儿怎么个拐法。看来别无他径,只能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来回逡巡于物象与笔墨之间,打量物象,思忖笔墨。弄清楚客观物体原本的真实特质和样貌:哪些是天生固有的,哪些是外在附加的;即便是物象固有的也要分清楚个取舍增减。而笔墨范畴里更是名目繁多:线和线的关系、墨和墨的关系、线和墨的关系;还有水的因素、色的因素加入进来以及这些个关系和因素搅合在一起对速度、压力、曲直、方向等条件的要求与反应,最终所有这些综合元素的聚合体所构成的诸种矛盾统统落实于柔绵而敏感的生宣上,再经由水分、轻重、快慢等敏锐而捉摸不定的外力作用,呈现出千变万化又引人入胜的样态。而这形形色色的笔墨样式和形态到头来都必须围绕着画家心目中之物象来组合、来调配。要落实、组合好上述这些关系和矛盾,使之各司其职而又相互融洽地完成物象的构建,从而塑造出生动别致的物象,都需要从容而理性地来归纳、辨析、分解、调和,以便使这其中每个要素之间有条理地和谐相融。当然此处的“条理”与“和谐”并不是一味儿地统一规整,而是指在充分把握宣纸和水墨特有的变幻无常之条件下,组织恰当、调配妥贴,有意识地利用诸如干和湿、浓和淡、粗和细、快和慢、方和圆、曲和直等矛盾的对比(在某些情况下,不妨可以人为地夸大、强化这些矛盾和冲突)使之呈现出颇有意味的笔墨情绪、笔墨倾向。而这些带有某种情绪和倾向的笔墨状态,一旦与画中物象——此时之物象已非自然界纯客体的物象了——有机而自然地融合在一道,基本上与画家先前期许的效果相距不远了。纵观历朝历代巨匠大家的绘画作品,无论是描绘的山川幽壑、风雨雪雾,还是人物风情、草虫花卉;或苍茫、或寂寥、或优雅、或蕴藉、或幽婉、或壮阔……不一而足。细细品味,比照着他们笔下的物象与绘画语言,都不难从中感受和辨析出大师们那超凡的转换本领,不管表现的物象情态是朴拙的还是潇散的;是细腻的还是雄壮的,一一无不弥漫着从容而悠游、恣意而笃定的气息和情怀。透过那一丝丝从容的恣意和悠游的笃定,我们分明看到呈现于纸面上的或枯或润、或焦或湿、或浓或淡、或急或缓的形形色色反差殊异的笔墨姿态与情绪;这些笔墨属性的姿态与情绪在一定意义是标志了某种特定的符号。虽然由于每个画家的个性气质相异,那些符号代表的含义有所不同,但它们反应和折射出的总趋向应该是大差不离,也就是说作品中每个符号分别应对着某种自然界客观物象之特性;同时也串联和沟通着画家在作品中蕴含和流露的意念与情怀。如果我们细心地审视揣摩就会不难发现,前面的那些应对和串联已经悄然完成了一种“转换”,一种由自然物象向着笔墨表现过渡潜行的转换。再如果,我们追根溯源地探究,此处 “转换” 的实现,实际上是由具有分别代表不同含义的符号来完成的。因为所谓“符号”原本是不存在的,它只是起到勾连客观物象与笔墨表现的一个跳板或桥梁的作用;而这符号的产生完全依赖于画家对客观物象之感受与笔墨表现之需求,在一定条件下,这些不同的感受与相同的需求经由画家开掘平日里的积淀、捕捉瞬间迸发的灵感、调和即时的笔墨以及融洽地驾驭这些积淀、灵感、笔墨等诸种要素(当然,这里肯定少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前提:画家本人超凡脱俗的见地和境界以及运用自如的技能和手段)在此基础上造就的“符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远不是纯机能而无生命的客观表象,此时的符号大大的蕴含着自然界林林总总物象的气息和画家内心与笔下欲图表现的主观意识。实践证明,唯有如此,在一幅写意画作品中,才能完成理想的顺乎画家意图的“转换”,从而,创作出具有意蕴和品味的作品来。
当然,说归说,做归做。实际实验起来,少不了许多许多具体而琐碎的事情需要去磨合、消解。这其中肯定夹杂着此消彼长的困扰,也免不了层出不穷的尴尬——是烦心的事儿也是开心的事儿。说烦心,是因为要厘清并调理好那么多的头绪,有条不紊地妥善处理它们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最终每个环节都熨帖妥当而丝丝入扣,是非常耗人心力的。说开心,恐怕也是同样的理由:那些自然界杂色纷呈有生命、无生命的芸芸众像,需要我们去感受、去辨析、去归纳、还要去整理;另外,中国画笔墨语言里那么多千差万异的形态和情绪,都诱引着我们去体验、去揣摩、去玩味、去享受。虽恼人却也很愉悦,一旦入了进去很难自拔——也可能并不想拔。说到这里,我不得不修正一下前面讲过的那句“做的比想的和说的都要难得多”的话:多说不如多想,多想不如多做。
2009年小暑于南京艺术学院
(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中国美协会员)
上一篇:于友善—蕴藉的激越

 吴光宇
吴光宇 王霄
王霄 王轶琼
王轶琼 庞明璇
庞明璇 未知
未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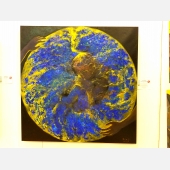 郑霞娟
郑霞娟 黄琦
黄琦 贾平西
贾平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