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友善—线条的困惑
2014-04-16 16:11:07
线条的困惑
于友善
【摘要】 不分今古,无论西东,在各色各样绘画作品里,线条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在中国画领域里线条的重要性更是凸显弥彰;不管是人物、山水、花鸟,也无论工笔或写意,线条几乎支撑和统领了整幅作品的骨架与形貌,甚至它在作品中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画面的气息和意蕴。历经时代变迁以及画风演变,往往在完成画作时,线条承负着双重甚或多重的义务,以至于有时候在一幅描绘纷繁复杂物象的画作里竟然反客为主,线条一跃成为画家追求和观者品赏的主要目的和标准。这无疑增加了线条的难度——是线条的困惑,同时也是经常袭扰画家的一个困惑:不得不殚精竭虑挖空心思地去琢磨、去探究。而绕有趣味的是,尽管如此,依然有那么多的中国画家终日里心甘情愿地乐此而不疲。
关键词:轮廓 形状 意蕴 精神
我——一根普普通通、间间单单、平平常常的线条,既不知生于何地,也不知始于何时;羞于自己太过寻常,我无意于抛头露面。可偏偏有人喜欢拿我来说事儿,评头论足的有、说三道四的也有;更有甚者那些好事者还给我分派了国籍,区别了今古。特别是那些玩国画的,一会儿把我捧得云里雾里,奉为至宝;一会儿却又抛来丢去,嗤之以鼻。不过,我自己清楚,不管怎样我还是我,一根线条,一根不起眼的线条。
自打落户到中国画这个圈儿里,有一阵子我好像顿时倍受关注,时常被那些画家们拖来拽去、抻长缩短、捋直撇弯、捻粗搓细;整日介摩挲盘玩无非想让我服役于他们,听任使唤,用来顺手。说实话,最初我的任务还挺简单:就是替他们笔下的玩意儿圈出个形状,勾出个轮廓,或是人、或是马、或是山、或是树,再不就云啊水的、日啊月的——简单。除了任务简单,我自身的装束也简单:通常是一袭墨黑,粗细均匀、干湿适中,没别的。回想起那阵子真是轻松——除了为某个劳什子框出边缘形状,再没别的附加的事儿。自由自在、任意恣纵,随心所欲地游走于岩石洞壁、陶盆瓦罐、木板竹片、兽皮龟甲之上。有时人们也会给我们差遣两个助手,赭红或乌黑的矿物质材料,半稀不干地平躺直铺在由我们圈定的形状里。说是“助手”,因为它们实在是不那么重要,可有可无,不起眼。不管在哪里亮相,我们总归是主角儿,也最吸引人们的眼球。到了后来,我们活动的场所变迁了,干活的范围也扩大了,有屋宇壁墙,也有素帛纸绢。说实在,更换场所对我们来说倒不难适应,让我们觉得负担加重而头疼的是,劳作的性质和内容与以往不同,不仅仅像前辈们画圈定形那样简单了。主人(也就是那些画家)要求我们强身健体,有力量、有韧劲,身姿曼妙还不乏弹性。不管行走到哪里都显得那么精神、鲜活,勃然而富于生机。特别是后来领着我们行走在软绵绵、遇水就渗的一种叫做生宣的薄薄纸面上,越发别扭而不自在。更麻烦的是,要我们行走起来由以前的匀速变为时快时慢,姿态也一改先前的直立而为或正或偏、或侧或卧,挪移的脚步有重有轻,携带的水分或多或少。通常走完了回过头来看看行进轨迹,我们的形态由从前的粗细一致、浓淡均匀转而变化成干湿、浓淡、曲直、粗细、长短、方圆都不重样儿(据说,那些分布遣派到国外的线条伙伴儿们的劳作远没有这么繁复,比起我们轻松惬意多了)用主人的话来讲,这完全是看重我们,谁叫我们一直以来盘踞在东方,固守于中国最终落户到国画这个范畴里呢?于是乎我们行动方式和劳作目的由老早的框定轮廓转而成为独立表现——真正地绝对主角儿。时间一长,我们也确实觉得自己地位高了、身价也高了。不经意间飘飘然目无旁人堂而皇之地长驰直驱、登堂入室。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画家将我们一举晋升为国画中所有参与干活的伙计角色(如颜色,墨块等等)的领军人物——挑起了大梁。这突如其来的角色重新定性,名次排前,职位提升,让我们觉得既受宠若惊又深感负担加重。不过这样也好,只要在中国画这个活动范围里,听任主人调配差遣,任劳任怨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心无旁骛,逆来顺受地恪尽职守,终了让主人说个好就行。本以为这就可以了,但渐渐地发现,画家们并未就此而心满意足。他们并不罢休,嫌我们的活计过于单调,过于平淡,还要在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里添加更多更细更繁杂的内容:有的要表现犀利、有的要表现温和、有的要表现雄壮、有的却要表现委婉……还有多样混杂,也有重复兼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问题是,在额外增加了那么多负担后,并未打算卸掉或减轻我们以前的任务——也就是早先的框定形状,划出轮廓。这很让我们干起活儿来不免分心,也分外吃力。试想,谁能在双重甚至是多重压力下仍旧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地做好工作,但画家们却不顾这些,硬是要我们来履行。所谓多重任务,就是要求我们除了最初给物象勾定轮廓形状,让观者一看就明白画家描绘出个什么物体之外,更要我们在描绘过程中自身显示出某种精神和意蕴来;这些精神意蕴直接明示人类的某些情感流露:比如愉悦,比如激烈,比如冲淡,比如蕴藉——很多很多的“比如”。这还不算,不知始于何时,竟然有人自说自话地把我们本属一体的哥们姐们硬生生分拆离间而为什么所谓“十八描”,其中有好些读上去拗口别齿,分门别类,无奇不有:有似菜似草的,也有兽类鸟类的,有往打仗兵器上靠的,也有朝劳动工具上黏的。真可谓五花八门(其实,这‘十八描’里大约估摸一下,统而拢之也不外乎只有两类:一类是有着粗细宽窄顿挫变化的,另一类没什么变化,一路匀溜顺畅)但我们还是我们,该干什么依旧干什么。可是,活儿干多了,时间一长,劳累复加厌烦,大家自然也长了脾气。画家眼尖,似乎也摸透了我们,非常敏感地逮住这点,顺势给大家划分出这样那样各不相同的性格类型来,有敦厚温和的、有调皮灵动的、有内敛沉默的、有外向张扬的,还有各色各样混杂型的……其实,原本我们自己并不清楚这些,硬是被那些画坛老手一味地捏弄出这么多花样来的;而且还要拉郎配似的给我们搭上不同的对象:软的配柔的、硬的配刚的,调皮配潇洒、内敛配浑穆,还有什么湿润适合恬淡、枯涩应对苍辣等等;这与其说是对号入座,依我看倒更像是生搬硬套。更有过分者有时候不由分说冷不丁地将起我们提溜起来就往一滩淡水稀墨里抛撒开去,呛着淹着且不说,还没等身上干爽利索,早已被浸泡得没款没型了。再不就趁我们刚在一块空白场所刚刚落脚歇息,还未缓过神来,便迫不及待地将大块湿乎乎的浓烈颜色劈头盖脸泼将过来,弄得我们都认不出自己原先的模样。而那些画画的却偏要说这样全是在为我们打扮妆靓,让我们与那些稀汤寡水艳色浊墨掺乎搅和在一起,更有魅力——真是天晓得!这还没完,要命的是如此这般地折腾一番之后,仍免不了遭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是这一拨儿欠功力就是那一伙儿乏火候,有气无力,没有精气神;要么怪我们过于剑拔弩张、妄生圭角,好自我表现,过于炫耀,过于张扬。真让我们左右不是,进退两难。有时挺泄气,真想甩手不干,但回头一想,不行,若要真的那样,我们这一大帮伙计到哪儿去?又能干些什么?有一阵子,被几个搞油画的拉去,调遣我们在又糙又涩的亚麻布上干活,成天和那些又粘又腻浑身上下充斥着怪味儿的颜料伙计搅合在一道,别扭死了(好像还听说有人给这样的活计冠以美名:‘油画民族化’,要晕)眼看不行,大伙儿只好重新调转回头,还是奔原来干活的场所。牢骚归牢骚,内心里我们还是惦着这块熟悉而又自在的环境——毕竟在这儿呆了那么那么长时间,少说也有两、三千年了。(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或许是同出一门的缘故,在这块熟悉又自在的场所里,还有一处特有缘领域——书法。记得有一位名人曾说过:“书画同源”。照此说法,我们时常是在国画和书法同一血缘的两家亲戚里来回打工;这两家子亲密的几乎不分彼此,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竟然分不清它们谁是谁。尤其是在篆书和草书那里,我们施展起来更是从容而洒脱,就像游走飘荡在写意画里一般。不管是国画还是书法,和它们相处,总是那么惬意、那么舒坦,彼此间那么融洽。
话虽这么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自由还是受到限制的。大家除了各司其职,按部就班做好分内工作以外,还要有团队协作精神,不可以随心所欲地自说自话,不管干什么,也不管往哪儿走,不仅得看主人的眼色,还必须顾及同伴的动向。一定要与大家随时保持联系,走得太快太慢不行,离得太近太远也不行,(为此,好像还专门有个词儿来形容:叫什么‘密不透风,疏可走马’,不过,如此这样搞多了,搞过头了,也挺让人烦,做作)彼此间必须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照顾、相互呼应。行动起来有时要勾肩搭背、摩肩接踵,有时则应似断似连、若离若即,肥头胀脑肚子里灌满水的扎成一堆,瘦骨嶙峋浑身干瘪的凑在一块,高个子要带好矮个儿,胖子也别落下瘦子……反正要按指令保持适当的距离、方向、长短、曲直——确实挺苦挺累。不过,说实话,经由这么统一调配,大家都暂时收敛一下性子,伙伴们之间多担待着点,最后排成的队形和布置的阵势确实蛮好看、蛮顺眼的。事实证明,经由时间的磨砺,渐渐地我们也适应了工作要求,麻烦也好,繁琐也好,都习惯了工作的性质。大家能够在完成任务时尽量做到积极主动,不松懈,不怠慢,争取上佳表现。俗话说的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的辛勤劳作也确实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就像褒奖那些先进个人或先进集体一样,我们有些伙伴出色的表现分别获得了嘉许:有的荣膺为“吴带当风”、“曹衣出水”,有的则冠以富于诗意的美名:“行云流水”、“如泣如诉”……等等等等。好在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在荣誉面前也并未头脑发昏。大家都知道,所有那些美誉的得来并非单靠我们自己,这里面有历朝历代画家才情的投入,同时断然也少不了许多在意、关注、欣赏我们的人们一直以来的关怀。否则,画家再怎么厉害,我们再怎么卖力,如果没人搭理、没人在乎,没有那些能读懂我们的人来理会,也全是白搭。当然,我们也很心里清楚,除了极个别场合,大多数情况下,一幅形、色、神俱佳的画作的诞生,并不全然是靠我们单枪匹马孤打独斗自个儿完成的。这里面多亏了好些别的团队伙伴们的照应和支持;假如没了颜色、墨色、物形乃至于整幅章法的支撑和帮衬,再有多大的能耐,任凭如何蹦达,恐怕也无济于事。所以,我们时常提醒自己,即便有多大本事,在别人眼里是个主角,也要有自知之明,与所有伙伴处好关系,别自以为是。这也是多少年来的经历体验总结出的一个道理。
不过,正如老话说的,苦恼随时都有,往往是这儿才消停那儿又冒出。其实,前面讲的所有那些困惑,、繁琐、劳累、折腾,我们都能扛得住,苦点,累点,烦点,腻点,没啥。真正让人受不了、有苦说不出的倒是,弄的不好什么时候时运不济、阴差阳错地摊上个没头没脑,没能耐、没本事的主儿,那才叫倒霉。他既摸不透我们的性子,我们又揣不出他的意图,舛误抵逆横生,牴啎芥蒂频现。最难以忍受的是那些主儿还特喜欢把自己当回事儿,蹂躏糟蹋我们不说,还时不时煞有介事地翻弄些新花样,搞一些怪名堂;似乎不把伙伴们折腾得面目全非死去活来绝不善罢甘休。于是乎,一些不伦不类的、不土不洋的、牛头不对马嘴,什么样的都出来了。非但把我们弄得稀里糊涂,更让观众看得一头雾水;这还不够,动不动还硬是强加给我们许多古里八怪的名衔,装扮些莫名其妙的饰头,美其名曰乎“创新”、“个性”。不是隐含了“哲学的意味”就是蕴藏了“宇宙的律动”。说真的,与其这样,还真不如把我们派到那些新手下面干活。他们可能由于缺乏训练而显得生涩、僵硬,彼此间相处时有疙瘩,保不齐有时还会生出矛盾抵触,但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至少,那些新手们对待我们的态度是挺真诚、也挺实在的。相比之下,我们大家都很不情愿和那批半吊子的所谓“大师”、“名家”相处共事,内心委屈浑身别扭不谈,最糟糕的是,我们原本还算清白光亮的名声,经由他们这么一胡搅蛮缠全给毁了。老天保佑,千万别让我们摊上这样的主儿,谁晓得——难道这不都是推不了撇不开的困惑吗?
2009年 黄梅季节于黄瓜园
(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中国美协会员)
致谢
尊敬的《东南文化》编辑:
非常感激贵编辑部的指导意见,如线的概念(线在绘画艺术的与数学物理的不同领域中)、线的历史发展过程、线条并非唯独今人为之困惑、线在绘画作品中的美感认知理应由包括作者与欣赏者共同完成以及“书画同源”问题等。接下来笔者尽力在上述范围内根据编辑部的意见作了调整和修改。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同时也基于其他考虑,文章的行文方式以拟人化手法来进行书写,可能也是因为叙述此类话题的文字太多,亦属不得已而为之。
再次感谢﹤东南文化﹥编辑部给予本人这样一个求教的机会!
于友善

 吴光宇
吴光宇 王霄
王霄 王轶琼
王轶琼 庞明璇
庞明璇 未知
未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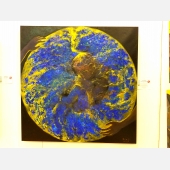 郑霞娟
郑霞娟 黄琦
黄琦 贾平西
贾平西
